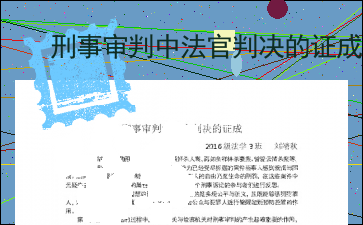刑事审判中法官判决的证成
以下为《刑事审判中法官判决的证成》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
刑事审判中法官判决的证成
2016级法学3班 刘某某 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到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再如佘祥林杀妻案、曾某某情杀案等,一个个冤假错案的产生令人触目惊心,人们纷纷为已经受尽折磨的案件当事人感到惋惜与同情。然而,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可以剥夺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的刑罚,在这些案件中无疑失去了它公平与正义的属性,这也不得不让整个刑事诉讼的参与者们进行反思。
应当认为,一个最为理想的刑事判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平与正义,且既能够惩罚犯罪人,对受害者尽到心灵慰藉的作用;又能够对社会公众与犯罪人进行警醒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第一,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侦查机关拥有实施勘验、检查、搜查等一系列侦查行为和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被滥用,侦查机关往往会刑讯逼供、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从而导致非法证据的产生。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又拥有对侦查结束后案件的审查起诉权以及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进行合法性监督的权利。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刑事犯罪侦查机关的侦查程序进行合法性的监督以及不能对侦查结果进行审慎的实质性审查与实在法上的非法性审查(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就会使得非法证据在审判中适用或者无罪者接受审判,从而导致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失真。
因此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必须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负有全方位的保证其合法性的义务,这个义务既包括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也包括程序法上的合法性。到如果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程序法的合法性更应该值得被保护。继而,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对刑事诉讼的非法性进行前置性控制,避免“带病审判”的产生。
第二,审判机关作为唯一有权确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机关,承担的是最终裁判者的角色。首先,从横向上看,只有审判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提出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以及对起诉过程中法律的错误适用进行纠正;然后,从纵向上看,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不同于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等。相比之下,我国刑事犯罪的被告人通常只有一次上诉的权利,因此每次判决的结果都显得更加至为重要;另外,从管理学上的角度来看,更改一个已经做出的决定往往比最初做出一个决定更为困难。这一点在国家机关中无疑会被成倍的放大,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刑事判决的更改,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中,经常不仅仅是法律的问题,更包含着一些保持政治平稳、维持社会稳定的因素;最后,进行刑事审判的法官具有代表国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权利,相比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或者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是一种最严厉的甚至可以剥夺人生命的强制性制裁方法。
综上,我想说的结论是,刑事审判中的法官必须承担着整个司法流程中最为沉重的义务。
所以,刑事审判中的法官这一个最为重要的义务是什么呢?即是对一种对刑事审判的证成义务。根据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九条的规定,法官应该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正确适用法律,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主观臆断、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但是这一条显然是一条总括性的规定,法官判决的案件是否公平公正应该如何断定?法官的判决确保公平公正应该达到各种程度?这些都无法回答。反倒是修订前2001年开始实施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给出了答案,即——第一条,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遗憾的是,这一条在新修订的《准则》中并没有对应的条文。)
也就是说,法官的通过对判决的证成,必须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这不仅是对法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名最优秀的法官所必备的素质。卡多佐大法官曾经说到:在这些问题上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进而,刑事判决中,法官对判决的证成必须遵循四个原则——逻辑证立原则、经验证实原则、实在法证成原则、以及“衡平与正义”原则。
下面将以曾某某案为例子来分析这四个原则的要求与其内在价值。
第一,逻辑证立原则:法官裁决要遵守逻辑理性,所做的裁决必须要经得起逻辑理性的推敲。
在“曾某某”案里,2015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书中,关于曾某某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卷宗中没有收集曾某某手机短信内容这一关键证据,导致证明曾某某无罪的物证缺失”的问题,湖南省高级法院对侦查机关没有收集手机短信内容这一证据的原因的答复是:第一,李某甲的这一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且从李某甲的证言本身来看,主要系其主观推断,内容也不确定。第二,一审通过对曾某某、陈华章的供述及李某甲的证言分析,认定曾某某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并无不当。
从逻辑理性来看,第一条原因的认定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错误。
没有对短信内容这一证据进行搜集,是因为法官认为李某甲本身的证言内容不确定,系其主观推断。换句话来说,法官认为李某甲的证言本身不具有客观性,是其主观的推断。
这个推论在逻辑上存在错误。如果法官的推论成立,李某甲的证言因为不具有客观性而排除其真实性,那么法官的主观判断:“李某甲的证言因为不具有客观性而排除其真实性”也会因为没有对曾某某的手机短信的内容是否存在——这一关键的客观性的证据进行收集而得不到支持。(因为法官正是以客观性为出发点进行了判断,而以客观性为出发点,在逻辑上必须保持自身的客观性,否则就会导致自证自错。)
第二,经验证实原则:法官的裁决要尊重客观事实、经验常识和自然法则,所做的裁决必须要经得起经验理性的批评。
法官对不予采纳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同逻辑证立原则的辩护意见)的第二条解释是:一审通过对曾某某、陈华章的供述及李某甲的证言分析,认定曾某某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并无不当。换一句话说,法官认为:一审的判决认定,检察机关提出的曾某某具有作案时间这一结论因为证据不确实、充分而已经予以排除。进而,辩护人提出的“检察机关未提取手机短信内容这一证据,从而导致证明曾某某无罪的证据缺失”这一辩护,因为辩护人提出这一请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从而对辩护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可以看出,二审法官认为辩护人在上诉的过程中提出这一辩护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曾某某不具有作案时间,从而证明曾某某无罪。然而,根据一个社会上普通人的经验,一个已经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处无罪的人进行上诉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继续请求法官认定自己因为证据不足而应该被判处无罪吗?
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可以根据经验法则明显的推断出,辩护人进行这一辩护的目的是为了请求法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而对被告人作出依据法律认定的被告人无罪。而绝非一百九十五条的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该作出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总而言之,二审法官根据所提出的,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的两个理由分别得不到逻辑证立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的支持,是经不起批评的,甚至说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实在法证成原则:尊重实在法规则,任何判决都应该得到实在法法律上的支持和实在法精神上的支持。
2010年6月25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曾某某判处的死刑立即执行,明显不符合实在法的规则与精神。
《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说刑事判决应当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文是少有的几个刑罚倒置,将死刑排在第一位的条文。对比故意伤害罪的条文——“犯一般伤情的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可以看出,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区分是一般情节、严重情节、和特别严重情节;而故意杀人罪的区分则是一般情节和较轻情节。刑法之所以将故意杀人罪的区分分为一般情节和较轻情节,是因为故意杀人罪是危害人生命的最为严重的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即被害人的生命已经因为犯罪的实施而消灭,无法再考虑客观上对被害人的危害结果。因此,刑法首先考虑给予其最严厉的刑罚措施,再在其基础上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给予相应的刑罚。这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定罪量刑思维过程,例如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是在一般情形的基础上,主要考虑犯罪人的客观危害结果,再结合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综上,对于故意杀人犯的刑罚裁量,着重考察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而不是犯罪人的危害结果,因为犯罪人的危害结果——被害人的死亡是既定的事实,刑法已经给予了判断——对犯罪人刑罚从死刑开始考量。因此,法官应当充分考察犯罪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社会影响、是否为累犯、杀人的手段是否极其残忍、是否杀害多人、被害人是否有过错、犯罪人是否立功自首或者事后有无悔恨等情节,来综合考察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做出判决。并根据这些情节来证成自身判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做出的判决中,法官未能考虑到的情节至少有五点。一,曾某某并非累犯或者具有前科,而且初犯。二,曾某某仅杀害被害人一人。三,曾某某使用了常见的勒杀作为杀人手段。四,曾某某的犯罪动机是受到被害人的诽谤,心生愤怒而杀人;相比于曾某某,陈华章因被害人比其优秀,产生妒忌而杀人更显得恶劣。五,被害人生前曾诬陷曾某某有过嫖娼经历,具有过错。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也从侧面反应出,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初未充分考虑曾某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而直接适用死刑,是不符合实在法的规则和精神的。
第四,“衡平与正义”原则:法律应该与社会之间形成“完美的契合”,法律要回应社会对公正与正义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二十条规定:注重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积极寻求有利于案结事了的纠纷解决办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曾某某”案中,社会大众对审判的结果具有很高的期待,人们普遍希望能够惩治真凶,实现正义的要求。但是,除了对实体正义的要求外,人们还有对程序正义的要求。这两种最基本的要求必须在法官判决的证成的得到体现,法官也负有向社会证明其判决具有实质正义和程序公正的义务。从而回应社会对法律的期待和要求。
法律的精髓是理性,一个没有理性的法律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无法接受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明了,理性更是司法的底线,是法律人的良知。因此,法官的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败坏乃是正义的源头。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法官必须以自己的判决自证清白。
以上为《刑事审判中法官判决的证成》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上面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
图片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