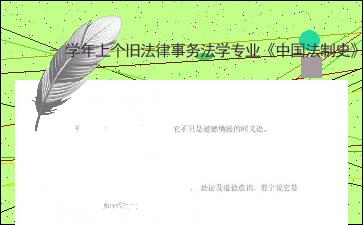-学年上XX法律事务法学专业《中国法制史》期末考核(A)卷
以下为《-学年上XX法律事务法学专业《中国法制史》期末考核(A)卷》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
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2021-2022学年(上)学期(函授)2019、2020级
法律事务、法学(专升本)专业《中国法制史》期末考核(A)卷
专业:法律事务 年级:2020级 学号:20B***姓名:袁嘉标题:《论“春秋决狱”》
论“春秋决狱”
一、从技术到理念:汉代“春秋决狱”的法律思维
?
一提及“春秋决狱”,但凡对中国法律史稍有了解者就会立即想到“原心定罪”四个字。确实,董仲舒自己也指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某某。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②]这似乎表明“春秋决狱”的要点单纯在于探讨犯罪动机的善恶。但是,此种焦虑只涉及法律事实的认定,它并不是“春秋决狱”所论案件的真正疑难之处。《汉书?QR宽传》说:“汤由是?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绝疑狱,甚重之。”《汉书?张某某》则记载:“是时,上方?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某某,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显然,《汉书》的阐述一直都在强调“决疑狱”时的依据。于是,QR宽善论经义而得重用,而作为酷吏的张汤也不得不向博士弟子求助。这些现象证明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春秋决狱”所涉疑难案件的困境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规范适用上的权衡。从这一角度分析现存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案例将进一步强化此处的观点。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某某?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某某。《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③]在这个案件中,事实是极为清晰的,问题的症结在于甲与乙的养父子关系能否成为隐罪的合理前提。在汉宣帝之前,汉朝并未在法律上真正规定“亲亲相隐”原则。因此,依照汉律,即使养父子关系可以成为实在的理由,也不可能引致“亲亲相隐”的结果。在儒家学者看来,这显然不符合宗法社会的理念。于是,董仲舒就以《诗》与《春秋》的“微言大义”做出判决,而此种判决则更具可接受性。在他的逻辑推理中,大前提只是儒家经义,因为法律本身并未就此做出规定;小前提是案件事实;结论则为“不当坐”。可见,在这一过程中,儒家经义起到了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在另一个案件中,儒家经义的功能就有所不同了。
本案的事实依然清晰,问题则在于尽孝反害父的做法是否具有可责难性。“或曰”明显代表了法律的意见,但在《春秋》看来,法律的判断是极不合理的。这里,董仲舒的论证逻辑首先将大前提扩大为法律和经义两种要素。他的主张与其说是排斥现行法本身的有效性,毋宁说是指责法律适用于某种特殊情形的不合理性,其目的仍在于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经义实际上一直发挥着评价现行法律规范之合理性的功能。通过对上引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董仲舒认为,较之现行法律而言,儒家经义必定更符合世道人心的要求。因此,经义应当改造法律、介入判决。这种构想使得判决的依据不再局限于法律本身,而真正合理的判决则必须综合考虑法律与经义。
紧随于此的问题就是,经义成为判决依据的正当性何在。答案似乎不能从法律本身推衍出来。事实上,“春秋决狱”以及它所推动的法律儒家化都是汉代整体制度建设的一部分。而这种制度建设又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否则制度的各种要素之间就难以形成一致的话语。然而,在尚力政治膨胀所引致的秦朝极度专制统治崩溃后,初兴的汉朝又囿于国力衰弱、知识储量不足等原因,无力关注这个根本性政治问题。困境的蔓延使汉帝国只能采取黄老政治这样的权宜之计。至汉武帝时期,经济、政治、学术等的发展使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亟待确立。此时,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了天道统摄下的整体法律观,“春秋决狱”则只是它在司法上的体现。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某某,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⑤]“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⑥]可见,法律的正当性即在于它的法天精神。既然天尚德,那么在具体判决中酌情考虑道德伦理因素就是必要的。而在儒家学者看来,最真实地反映天道理想又充满道德论证的文本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⑦]于是,经典介入法律的合理性就因天道关怀而获得了彻底的论证。然而,仍须注意的问题是,这种论证的根据并非来自于法律本身,而是源于理想的政治设计,其实质则是评价现行法的合理性。事实上,正是这一点推动了中国古代理想法模型的形成。
综上所述,“春秋决狱”在法律上具有双重功能,其一为填补法律的漏洞,其二为评价法律在个案中的运行状态。这二者在目的定位上是一致的,即以法律与经义并用的方式加强判决的可接受性。而论证经义本身之合理性的过程则引申出了更具根本性的法律图景。这些法律思维模式在董仲舒时代之后的法律史进程中不断转换自己的形态并型塑着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类型。
?
二、评价功能的发展:古代法的理想模型
???
????如上所述,“春秋决狱”对判决依据之合理性的考量具有评价现行法之正当性的功能。它的目的实际上是改造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律以为一种儒家化的良法。在董仲舒时代,这种阐释被无限上升至天道层面。由于它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在宗教观上的天道信仰,因此它成为后世学者在理想法问题上的通见,其区别只在于后世的论述更加具体化。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古代的理想法模型呢?问题似乎还要回到历史文本中加以考察。
《汉书??刑法志》出自于儒家学者班固之手,而班固生活的年代正是汉朝儒学鼎盛的时期,因此它所反映出来的观点代表了汉代儒家学者在理想法形态上的成熟论断。《汉书?刑法志》说:
???
初看起来,《汉书?刑法志》开卷所论天与人的共通性似乎与法律无甚关联。但是,只要我们联想到董仲舒的天道法律观,就会明白其中的一切奥秘。从根本上说,《汉书?刑法志》开篇所探讨的天人关系恰恰体现了“春秋决狱”的理念性结论,即评价现行法的正当性。在儒家学者看来,整个宇宙是和谐一体的,其任何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有利于沟通的同质化素材。人类社会的动荡并不只是人类自身需要承受的病殃,其破坏力足以扰动整个自然秩序的安宁。因此,作为社会控制之重要手段的法律就必须则天而立,此亦为判断现行法是否为良法的本质性要素。同时,既然儒家经典对天道作出了全面描述,那么则天而立的同义语就是则经典而立。于是,《汉书?刑法志》就反复引用《尚书》来论证良法的形态。作为诉讼现象的“春秋决狱”所引申出来的理想图景因《汉书?刑法志》的规划而获得了全面发展,古代的理想法模型也已基本形成,即名义上效仿自然(以天为代表)的和谐,实质上则遵循经义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的和谐。
《汉书?刑法志》所构造的理想法模型绝非汉代儒家的哗众取宠式行为,《晋书?刑法志》的解释表达了同样的理念,而这种理念的重复则又证明了“春秋决狱”之法律思维的延续。《晋书?刑法志》论道:
?
显然,《晋书?刑法志》的主张开始于天人的共性,而终止于则天而行的设想,其中穿插了为儒家经典所崇敬的圣人的行为,这种论证逻辑与《汉书?刑法志》何其相似。这足以证明古代法的理想模型在前后相续的历史阶段之间的传承性。事实上,晋朝也确实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时期,其创制《泰始律》的出现则代表了汉以来法律成长的结晶。正因为这一点,刘颂主张不应在司法实践中援引除晋律以外的其它规范:“今昔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⑧]
如果说《汉书·刑法志》与《晋书·刑法志》的观点只能代表撰史者的理想,那么《唐某某疏议》的主张就是实在的国家立法的论断。
???
倘若我们将《唐某某疏议》的阐述与《晋书·刑法志》相比较,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显然,在《唐某某疏议》的视域中,制度设立本就来源于人的灵性,而这种灵性又是自然的恩赐。正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融,法律的制定才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同时,“一准乎礼”是唐某某在古代社会中获得的殊荣,这又表明其精神已经完全吸纳了儒家经典的内涵。在自然和谐与经典释义的双重裁判下,唐某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古代社会中良法的典范。恰当地说,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理想法的实在形态。这也正是唐某某一直为历代王朝所推崇的原因。
至此,“春秋决狱”的最初目标,即改造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典并推动法律的儒家化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评价实在法的思维一直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每一步开拓性进展都表达了这种思维的呼声。作为一种诉讼现象,“春秋决狱”以其对判决依据的论证最终影响到了立法,而立法的完善又规定了评价性法律思维模式的停滞。因为,立法的集大成者《唐某某疏议》代表了理想法模型,对它的改进已经不可能发生在根本理念上,众多革新只能表现为更适应实际生活的法律内容的添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通说的主张——“春秋决狱”在唐某某形成之后逐渐淡出了古代法的历史——是恰当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春秋决狱”的实践性法律思维,即综合考量法与经义以最大程度地促成判决的合理化。事实上,这种思维模式贯穿于唐以后的所有历史时期,尽管各个历史阶段所拥有的法典都因唐某某的示范效果而博得了理想法律形态的认可。站在这个立场上审视“春秋决狱”的延续性,结论必然是“春秋决狱”从未消失。
?
三、经义的多元替代:唐以后的考察
?
中国古代法在唐以后进入了一个理念稳定的时期,“春秋决狱”的弊病——随意出入人罪——也因儒家化法律的确立而得到纠正,其结果就是汉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诉讼形态的终止。为了维护现行法的权威和避免规范的多元化,唐以后的法典基本上都设置了严格依法为断的律文。“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⑩]《唐某某疏议》的这条规定也得到了《宋刑统·断狱》、《大明律·刑律·断狱》及《大清律例·刑律·断狱》的共同强调,尽管具体形态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法典似乎更多地体现了法家的余某某。商鞅认为:“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11]韩非也主张:“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12]在法家人物看来,人类的理性能够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定明确的规范,从而使所有人置身于“唯法为治”的理想状态中。这种理念在中国古代法典的生长期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律的细密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不过,其波及面并不限于此。确实,由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倡导,古代法典逐渐走向宽平,但是法律穷尽一切行为模式的理想并未完全消失,《唐某某疏议》的复杂化足为其代表。既然法律已经囊括了全部社会关系,那么严格依法为断就是可以理解的。这并未指明法典的儒家化只是一个幻境,其真意是指,法典的具体规定依然细密,只不过绝大部分条文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的主张。
尽管如此,包容一切的法律乌托邦主义不得不认可社会变迁的态势或实际情形的复杂所带来的法律的缺憾。《大清律例·名例》指出:“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某某,定拟罪名,议定奏闻。”沈之奇注曰:
?
显然,法律的孱弱在沈氏之注中极为明晰地展现出来。在诸种情形下,判决的得出就不单纯是法律权衡的结果,毋宁说是法与情理的综合体。这里,我们见到了“春秋决狱”的实践性法律思维模式的痕迹,区别只不过是与法律共事的判断准则从经义变成了情理。事实上,这正是唐以后的司法运行应对复杂情境的普遍做法,而此种考虑在律典上亦有所体现。
?
从前两条规定来看,司法官员遇有律所不载的情形,其第一反应必定是寻找现有律文中的类似规定以推衍出一个当然的判决。《唐某某疏议》就说:“‘其应出罪者’,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可见,这种推论的规范基础仍然在现行法律体系之内,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内部类推”。而从后两条的规定来看,司法判决的大前提就将越出现行法律体系的框架。
沈之奇对《大清律例·刑律·杂律》“不应得为”的注释说明,法律对某些情势束手无策,但这些事态又不符合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行为的正当性,因此司法部门必须向法律外部寻找判决的依据。正是因为这两个条文的规范设想是向外开放的,我们可以命之以“外部类推”。[15]事实上,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类推,司法官员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都是法律的缺陷以何种规范来弥补并最终强化判决的可接受性。在这一疑难领域,情理、经义等外在因素的介入就是无法避免的。一旦这种侵袭现象实际发生,“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与某种外在规范共同作用的实践性法律思维模式就会自然地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律典的条文只是对特定实践思维的概括性规定,如欲深入了解此种思维模式在司法中的实态,那么,我们就应当进入古代的判牍中寻觅其行踪。“社会事实的内部必然有着某种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正是在这种事实的深处,或许存在着比思想家们雄辩地主张着争论着的各种命题更为本原的思维架构和条理”。[16]我们先来分析唐朝学者白居易对虚拟案件做出的判决:
?
在这个虚拟案件中,乙与其妻离异的原因并不符合律所规定的“七出”之条,而只是出于“父母不悦”这样的情理权衡。对“七出”之条来说,它所反映的同样是儒家一贯追求的伦理性内涵。但是,从更广大的范围来看,婚姻关系的维系显然在于父母的认可,因为在古代,婚姻并非纯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它涉及宗法团体的利益与和谐。站在这个层面上立论,父母的认可实际上构成了法律的基础,而律典所规定“七出三不去”只是这种基础的部分体现。这里,我们发现,本案的判决是在综合了法律与伦理之后得出的,而这种伦理又来自于儒家经典的阐述,其论证过程与“春秋决狱”的相似性令人诧异。不过,作为一个学者,白居易在虚拟判决中的思考更多地关注经义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判决之规范性前提的多元化上,他并未实现某种程度的创新。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唐代的虚拟判词转向宋以后的实际判决,那么结果可能就是另一种场景——经义的多元替代。在此类情形中,可以适用的规范已经从经义与法的共事转向由经义、情、理、法集合而成的整体。基于此,我们可以根据宋以后的判决所依照的规范性前提的不同,将其区分为三种模式,进而探索“春秋决狱”之实践性法律思维的运行。
第一,纯粹以法为断的模式。下面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法律的能力:
?
在这两个案例中,司法官员都直接引用律或令,并将事实与律或令所涵盖的基本要件相比较,其立场具有明显的严格法律主义的痕迹。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及的那样,官员以法为断正是律文的应有之义,“凡律例有所载者”皆为司法官员应当遵循的规范基础,否则就会引致轻度的刑罚。不过,对这些事例能够坚定地以法为断并不足以证明司法官员在任何场合都会谨守法律的立场,它充其量只能阐发此种事实,即法律恰巧对这些情形作出了规定。
第二,纯以经义、情、理为断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判决的依据与前一种模式相比处于对立的一极。从根本上说,此处判决的规范基础完全来自于法律体系之外。
本案的判官韩竹坡对判决的依据显然有所考虑,他的意旨重在强调何某某为他人立嗣以谋财利的意图具有道德非难性。但在法律看来,为他人立嗣只要符合“同宗昭穆相当”的条件就不具有可责难性。法律仅仅思索“存亡继绝”的道德意识,却忽视了它的利益关涉。于是,韩竹坡就引用儒家经典并提倡“诛心之说”来弥补法律的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原心定罪”相当。更为关键的是,韩竹坡直接表达了“天理”的法律效力。这使得宋代理学所主张的哲学概念直接步入法律领域,从而强化了道德的感召力,因为它得到了强制力的有力支持。有时,我们甚至能看到判决书成为道德教科书的情形:
如果我们回到判决的依据问题,那么可以说,经义及作为其具体化的情理发挥了法律论证之大前提的功能。
然而,韩竹坡的判词并不能证明经义与情理等同。事实上,情、理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
?
在这两个判决中,我们所见到的“理”或“道理”根本就没有道德含义,它们所指向的只是民间的习惯性做法或者普遍认可的常理。滋贺某某在考察清代民事法源时指出:“在判语中所见的‘理’字,可以说完全没有使人感觉到朱子理学中的那种哲学性意味。”[24]显然,这个论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适用于宋代的判决,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主张:宋以后判决中所见的“理”本身就不仅指道德层面的“天理”,它包含了道德与功利两个视角。正因为“理”有“常理”之意,我们也发现了以“习惯”为断的实例,而“习惯”本身也可命之以“常理”的规范形态。
?
这里的“乡原体例”就是“习惯”的一种称谓。
????至于情,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它不只是道德情操的同义语。
?
在这两个判决中,“人情”二字何曾有一处论及道德意识,毋宁说它是一般情感的代名词。
可见,情与理都具有普通性心理内涵,它们也许是古人在生存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利益思考或者正常体悟。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经义、情、理三者的区别促成了判决的外部规范基础(相较于法律而言)的多样化。尽管它们之间某个部分的重叠也确为事实。在此意义上,“春秋决狱”所体现以经义补充法律缺漏的思维方式获得了明晰的展现,而且“经义”的形态开始转向多元并逐渐融入利益考量。
第三,兼以法与情、理、经义为断的模式。前文已经展示了情理及经义、法作为两极而互相排斥的情形,但在司法判决中更多的实态是情、理、经义与法并用。
?
显然,情理、经义与法在诸多判决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结构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以情理、经义调整法律的刚柔。
在前一个案例中,区日科不养其母致死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有相应刑罚的,但是“致死”的结果在情理上当被视为加重情节,所以区日科实受之刑是在法定刑之外再加上三个月的枷号。在后一个案例中,华玉诉陆梅宇之言所有夸大,但他本人已系受害人,在情理上可以体谅其因怒而出的夸大陈词,结果则是免拟。可见,法律的规定并非无效,只是它在特定情形中的严格适用不符合世人普遍认可的公允立场。这种论证逻辑正体现了“春秋决狱”在个案中评价法律以提高判决之可接受性的实践性法律思维,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区别,其原因当然源自律典对严格执法的要求。明代官员颜俊彦的论点清晰地表达这种理念:“当以七分法三分情处之。”[30]
此处,我们已经明确了唐以后司法判决之规范基础的多样化形态。然而,既然规范基础是多变的、抽象的,那么,什么样的判决才是最佳的呢?
?
在古人看来,最常见的判决也就是最好的判决。进一步的追问就是:为什么情、理、经义与法兼用的判决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认可?换句话说,为什么“春秋决狱”的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够一直延续到清代?答案似乎要求助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世出现了所谓“唐宋转型”现象。[34]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关系的变迁加快,法律关系亦因此而复杂化。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口压力无时不在。事实上,近世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充满竞争气息的。寺田浩明指出:“互让共存的理论完全得以实现只能是在同居共财的小家庭各自的范围之内。但是清代社会的现实却是一个个小家庭之间进行着激烈竞争而且沉浮无常的世界。”[35]这个论断虽然只针对清代而发,但却基本道破了农业社会的困境。农业社会的土地数量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长则既有助于土地的开发,又不利于土地的人均占有量的提高,其结果基本上就是生活压力的加重。在这种“水淹至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内化”的触角只在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现行法,所以也可比之为“类法律教义学的历史类型”。[40]对后者来说,研究的焦点则是法律史的“外部性”。在这个视角下的法律史成为一种审视社会状态的路径,因为法典及判决总是社会实况的反映。与“法律史的内化”相对应,我们可以冠之以“法律史的外化”的名号。法律史的两个侧面并不是分离的,内化的功能在于更准确地把握某一时期的法律的形态,这个任务脱离了外化所构建的历史语境是不可能完成的;外化的价值在于更全面地理解法律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但这不能依赖一系列错误的解读。因此,法律史的内与外就能互相融合并与其它历史现象共同叩开历史的大门。
既然如此,那么“春秋决狱”这个法律史论题的内与外又是什么呢?众多阐述实际上已经指出,其内在部分就是法律体系的建构(以理性法为指引)、规范多元的设计和判决可接受性的强化;其外在部分则反映了法律在古代社会中的功能,即维持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构建社会和谐。秩序观念在“春秋决狱”的视野中具有首要意义,因为和谐本就是秩序的表达。这正是一个特定法律文化类型的自豪之处,同样也是它的失败增长点,因为它总是能包容各种事态却无法突破理念的瓶颈。
[文章尾部最后500字内容到此结束,中间部分内容请查看底下的图片预览]请点击下方选择您需要的文档下载。
- 2020中考考点好题随堂练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 十四五规划意见反馈
- 《法治专题》教案
- 部编版六年级道德与法治上册全册每课知识点考点归纳整理
-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心得体会
- 高考历史考试大纲的说明
- 中外法治小故事
- 2020年主观题考试成绩公布及资格申请授予工作的通知(印发稿)
- 律师事务所简介【0107-2021】
- 法律知识框架(一)
- 供应商道德规范和商业行为准则(海外反腐败、反垄断
-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2.4”法制宣传日演讲稿
以上为《-学年上XX法律事务法学专业《中国法制史》期末考核(A)卷》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上面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