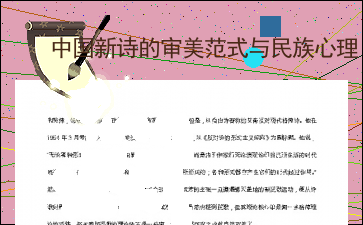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
以下为《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
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
张某某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一个民族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体制——诗歌依存的语言形态与美学架构,绝不是偶然、随意的选择,而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它往往暗接民族的深层心理,成为一种共同的审美范式。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都是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诗歌体制。
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一
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诞生不是本体演进、而是文学革命的结果。它不是古典诗歌的自然延伸,而是受西方诗歌影响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形式。它在语法、修辞、体制、美学等诗学的各个方面都遭遇一次断裂,而这一断裂迫使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发生错位。也许,这是新诗的“先天不足”。
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新诗不是由民间到文士,而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是新诗成功的纪元,而这首诗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从新诗创生期的作品来看,其主要特征在于以白话代文言,突破古典诗的格律束缚,创建自由体新诗。诗人们陶醉于“解放”的欢愉,再也不愿回到格律的牢笼。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某某》。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自诞生之日起,诗歌体制问题始终困扰着新诗的步态。围绕这个问题产生过四次大规模的理论讨论与创作实验,即20年代格律诗讨论、30年代大众化讨论、40年代民族形式讨论与50年代新格律体讨论。虽然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每一次讨论都推进了诗歌体制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0年代,宽厚的朱自清先生说,“许多人看着作新诗读新诗的人不如十几年前多,而书店老板也不欢迎新诗集。因而就悲观起来,说新诗不行了,前面没有路。路是有的,但得慢慢儿开辟;只靠一二十年工夫便想开辟出到诗国康庄新道,未免太暨急性儿。”现在新诗诞生80年,那么,它究竟离中国大众还有多远?换言之,这种诗歌审美范式距中国民族心理还有多远?
一种艺术样式如果不能深入民族心灵,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繁荣。从目前情况看,新诗还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圈里。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作为一种审美范式,新诗还未能契入现代中国人的心理,还远未深入民族心灵。也许,新世纪带给我们的将是又一次新的探索:新诗走向民族的心灵。
[文章尾部最后300字内容到此结束,中间部分内容请查看底下的图片预览]
以上为《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上面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
图片预览